企业社工在开展实务工作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环境扮演了多重角色,笔者以深圳市龙岗区中南社工服务所开展的企业社工实务为例,阐述了社会工作者如何将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付诸实践以解决服务对象所面对的问题,仅供企业社工领域从业者进行参考。
咨询者。咨询是社会工作者和企业员工建立关系的重要载体,咨询者是企业社会工作者最普遍扮演的一个角色,其“频率”贯穿了社工服务的始终。服务内容以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的咨询为主,社会工作者要亮明身份以便员工咨询,如制作身份卡牌、发放宣传折页、在活动中留取工作联系方式等,同时社会工作者要针对员工的咨询及时给与回应,为日后的服务打下基础。
联络者。企业社工是企业与员工之间沟通的“桥梁”,进入企业之初如何搭建“桥梁”就成了社会工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正在扮演联络者的角色。以员工需求为中心,本机构在实务过程中联络者的角色分为两种,一是企业内部沟通的联络者,二是对外资源筹措的联络者。在扮演企业内部沟通的联络者时本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实践:开办企业内刊,通过内刊通报企业重大事件及生产情况,宣扬优秀员工的工作事迹,收集一线员工心声和对企业管理存在的意见与建议。通过内刊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了解一线员工心声的渠道,也为新员工“传送”了优秀员工宝贵的工作经验;建立企业意见收集箱,定期收集企业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协助企业解决并反馈处理意见;年度的需求问卷调查,了解员工需求与存在问题,为企业领导者提供管理和制度修订依据。在扮演企业对外资源筹措的联络者时本机构的做法是主动寻求两新党委、人力资源局、文体局、共青团、妇联、工会、关爱下一代委员会、企业所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相关资源,及时了解政策资源的动态,积极主动联络对接。
促进者。当企业员工面临职业或生活困难时,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或小组工作的方法,帮助其分辨清楚所面临的问题,寻求出问题产生原因,并挖掘其自身潜能,使其问题得以解决,需求得到满足,此时社会工作者扮演着促进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情绪支持、潜能挖掘、资源链接等方式帮助困难员工顺利渡过难关。在资源链接方面社会工作者要掌握辐射到服务群体的政府公共资源和社会公益资源,如在深圳常用到有深圳市劳务工关爱基金、各个区的劳务工重大疾病医疗资助、重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会困难员工帮扶、工伤探视等资源,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可推动企业成立互助基金,拓宽员工支持网络以缓解其暂时的困难,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调解者。当企业与员工发生纠纷时,社工从中调处各方利益以顺利化解矛盾冲突,此时社会工作者正在履行调解者的角色,其频率最高的为劳资纠纷调解。社工在开展调解工作时要避免企业作为出资方购买社工服务和社工维护弱势群体之间的伦理困境,其理想状态为社工可以正真以“第三方”状态履行调解者的职责。以本机构开展的“和谐劳动关系社工综合服务项目”为例,该项目由龙岗区人力资源局采购,社会工作者真正做到了独立于企业和员工之间的“第三者”,在相关法律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指引下开展调解服务。社会工作者在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时可以尝试运用任务中心模式,通过清晰界定问题、明确界定服务对象、合理界定任务的工作步骤解决相关冲突。
教育者。就教育者角色而言,本机构在实务开展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教育,为员工提供充实和提高自己以胜任工作的机会,其典型的服务是组织开展新员工入职培训、生产技能培训、企业产品研讨会、安全生产培训等,在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全面统筹,积极组织,邀请企业技术专家或经验丰富的老员工进行职业教育。另一种是成长教育,例如链接资源为企业员工开展英语、吉他、瑜伽、摄影等兴趣学习小组,丰富和充实员工工余生活,促进员工正向成长。
倡导者。在宏观层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尝试通过“深而广”一线服务经验倡导国家相关政策;在微观层面,社会工作者要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法律法规,同时要倡导企业员工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本机构服务为例,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相关法律知识宣传活动就是在扮演倡导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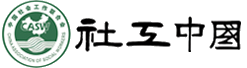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